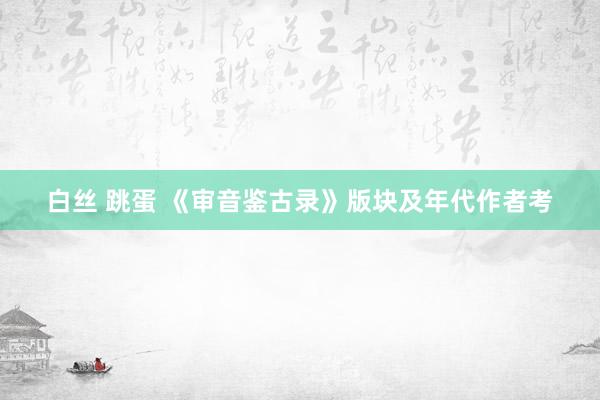
《审音鉴古录》是清代中世一部戏曲选本。中国古代的戏曲选本,常常发达为剧选、曲选、出选三种外皮阵势,或是像《元曲选》、《六十种曲》是全剧的书册,或是如《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是以宫调曲牌为编选体例,或是《缀白裘》一类收录杂剧、神话、戏文、花部的单出选本。《审音鉴古录》在体例上应属于其中的戏曲出选。所选曲目包括《琵琶记》一十六出、《荆钗记》八出、《红梨记》六出、《儿孙福》四出、《永生殿》六出、《牡丹亭》九出、《西厢记》六出、《鸣凤记》四出、《铁冠图》六出,合计九剧六十五出。该选本书前有序、每出正文前皆有一幅插图,书中有大量的戏曲评点府上。在古代迢遥的戏曲文件中,它别具一格,具有焦虑价值。内部许多的戏曲献艺批录,为究诘清代戏曲献艺、戏曲审好意思提供了珍稀府上,呈现出与其它戏曲选本迥异的特色。好多学者贵重到《审音鉴古录》选本的价值,如叶长海的《中国戏剧学史稿》辟专题“《审音鉴古录》论角色的创造”、“《审音鉴古录》舞台搞定例话”[1](P417-424);廖奔的《中国戏曲史》觉得“这部书是第一部特意的导演文章”[2](P275);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中集在“昆山腔的扮演”一节顶用了较长的篇幅分析了《审音鉴古录》的扮演艺术[3](P329-343)。《审音鉴古录》的专篇论文不是好多,大陆学者郭亮也曾分“科介讲明”、“曲白旁注”、“东说念主物上场之按语”、“眉批”、“总批”五种讲明体式对其进行分析[4](P54-59)。其实,《审音鉴古录》还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如它的版块情况如何,成书于何时,批录者是谁,都给咱们留住了疑问。本文尝试从现有文件及书中的批录府上熟识《审音鉴古录》的版块情况,预计其创作年代及作者,以期通过对三者的准确界定,激动对乾嘉时刻昆曲发展情状的潜入究诘。
张开剩余89%一
《审音鉴古录》一书成书虽晚(据书前琴隐翁序,成于说念光十四年三月,即1834年),但流传并不广。现在所知的版块有说念光十四年王继善补刻本,书前有琴隐翁序。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都门藏书楼、清华大学藏书楼等七家藏书楼保藏有该书。说念光本在我国主要有这样几种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影印本、学苑出书社2005年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发行的由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其中第五辑第73、74册影印出书该书,不外书品欠安,眉批处多有脱漏;学苑出书社2005年5月也原版影印该书,售价高亢;《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戏剧类)第1781、1782卷收录有该书,书前有“据上海词典出书社藏书楼藏清刻说念光十四年王继善印本影印,原书版框高二四三毫米宽二九八毫米”字样,印刷澄莹。比拟台湾书局、学苑出书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属于归拢版块——说念光本。
据《中国戏曲志·江苏卷》,该书还有另一版块——咸丰本,书中“审音鉴古录”词条云:“……不分卷。有说念光十四年刊本。另有咸丰五年(1855)王世珍(籍贯无考)重校刊本(藏南京藏书楼),增刻眉批,为说念光本所无;并有王世珍序,但无琴隐翁序。……”[5](P823);《中国昆剧大辞典》俞为民先生注释的词条“审音鉴古录”中也言明“南京藏书楼藏有另一咸丰五年(1855)王世珍的重刊本,增刻眉批,并有王世珍序,但删去了琴隐翁的原序”[6](P920),并附有王世珍序的书影图片。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究诘》也指出该书有“咸丰五年重刊本”、“有咸丰五年王世珍小引”[7](P254),则该书有第二版块——咸丰版当属不谬。既云咸丰版是“重刊本”,当与说念光版内容一致。不外《中国戏曲志·江苏卷》言说念光本莫得眉批,就不合适事实了,从前边所举三种说念光本影印蓝本看,都是有眉批的。俞先生言“王世珍本”“增刻眉批”,但未有详实的讲明,令东说念主猜疑。
说念光版卷首有清琴隐翁序:
“神话虽演义念,别贤奸,明治乱,善则福,恶则祸,天说念明显,验诸一会儿,无知贤愚不肖,皆足动其不雅感之心,其为劝惩感发者良便,未尝非辅翌名教之一端也。元明以来,作者无虑千百家,晚世善事尤多。撷其华者,玩花主东说念主;订以谱者,怀庭居士;而笠翁又有授曲教曲之书,皆可谓梨园之要领矣。但玩花录剧而遗谱,怀庭谱曲而废白,笠翁又空谈而无词,萃三长于一编,庶非氍毹之上,无虑周郎之顾矣。东乡王子继善偶于京师得《审音鉴古录》一编,选剧六十六折。细言评注,曲则朗朗上口,白则缓急高下,容则周旋进退,莫不迤逦逼真,展卷毕现,至记拍、正宫、辩伪、证谬,较铢黍而析芒杪,亦复大具苦心,谓奄有三长而不易之指南可也。继善念其尊东说念主琼圃翁生平音律最深,每叹时优率易流毒,念念欲手定一谱,兼训声容,著为准则,惜未成而逝。既获此本,喜与乃翁夙愿相侔也。爰转折购得原板,携归江南,稍事补雠,便公同好,第是编谁所评辑,一时无稽。继善不肯攘东说念主之功,特丐予序所自得并是以购之之故。嘻!继善之克慰其亲者,固不独此,然即此亦可见其能承先志。其辅翌名教又兼在动东说念主不雅感之区,一编已哉。说念光十四年三月上浣琴隐翁序。” (据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影印本[8](P1-8))
咸丰版卷首有王世珍序:
色播五月余素嗜词曲于弱冠,后专之于斯,不少拒绝,垂在已五十年矣,今已煞白倦倦,良可叹也。曩时宦已楚,公余之暇,散播书肆,购归必详加校勘,虽曲名颇繁,究其精妙绝少。兼坊间镂版鱼鲁之谬,度曲之家频频苦无专书,颇难审择,余搜择九种重加手校付之剞劂,以供后学同道者鉴矣。乙卯孟春王世珍谨识。(据《中国昆剧大辞典》书影图片[6](P920))
从两种版块前言看,其后的咸丰版小引篇幅短小,所述为个东说念主嗜好及东说念主生感慨,价值不大。但也可看出,从说念光版之后二十一年,坊间仍有此书发行,讲明此书在那时仍有商场需求。由于坊间刻印本多有不实,王氏进行了一些手校使命。可惜,前言说的仍然很不了了,如他遭受的“九种”版块是若何的,有无注明编选者(昭彰王氏并无此方面的闭塞),同期亦未对该书有任何评价。
说念光版的价值远比咸丰版为高。前言除对《审音鉴古录》一书出书始末缘由、内容特质进行了先容;还在戏曲不为东说念主敬重的情况下,开篇对戏曲的价值功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觉得“神话虽演义念”,却有“动其不雅感”、“辅翌名教”的功能;并以历史的目光看待戏曲批评发展,贵重到了那时戏曲剧学文章更生的欣喜;另外,还从横向比拟的角度分析了该书与其他戏曲选本、论著如《缀白裘》、《纳书楹乐谱》、《闲情偶记》的不同。不错说,前言作者是畸形有远见远瞩的。
二
《审音鉴古录》前言的末尾签字琴隐翁,查《清东说念主室名又名字号索引》[10](P498),琴隐翁是清朝画家、文体家汤贻汾的又名。各词典对其先容大体通常,《中国文体家大辞典》较为详实一些,“汤贻汾(1778年-1853年),字若仪,号雨生,晚号粥翁,江苏武进东说念主。生于高慢宗乾隆四十三年,卒于文宗咸丰三年,年七十六岁。以祖父难荫,袭云骑尉,为三江守备,历官粤东、山右、浙江,儒雅廉俊,伏莽帖弭。后以抚标中军参将,擢温州镇副总兵,因病不赴。退隐白门,贷“保绪园”以居,焚香饱读琴,翛然尘外,海内名宿多与之游。洪杨之乱,白门陷,赋绝命诗,投池死。谥忠愍。贻汾工诗字画,著有《琴隐园诗词集》、《画筌析览》。亦精音律,制有《梯仙阁三种》(墨林今话),令家婢歌之,咸能上口”[11](P1654)。汤贻汾主要的成即是在绘图,同期工诗书,亦是一位戏曲作者,著有《梯仙阁三种》和杂剧《狂妄巾》。
那么,汤贻汾是否此书的编选者和评注者呢?小引中提到二个东说念主物,王继善和他的父亲琼圃翁,言明该书原版由王继善购得,为完其父遗志,王补充校对后刊印此书,但不肯居为已功。查阅府上,王继善和他的父亲琼圃翁未见史料纪录,那么会不会是小引作者出于某种原因的虚托之词呢?
《审音鉴古录》批录中一共出现过两个那时东说念主物,一位是孙九皋,见于《荆钗记·开赴》总批,“此出乃孙九皋首剧,身体虽繁,俱系画景,只怕失传,故载身体”[8](P324);另一位东说念主物是陈云九,见于《牡丹亭·冥叛》眉批,“地字工尺,教习陈云九传”[9](P611)。这两个东说念主物均见于《扬州画舫录》。《扬州画舫录》卷五对其纪录是“小生陈云九,年九十演《彩毫记·吟诗脱靴》一出,风致横溢,化工之技”[12](P122),“老外孙九皋,年九十余演《琵琶记·遗嘱》,令东说念主欲死”[12](P126)。
《扬州画舫录》一书发行于1795年,书中记录多为作者同期代东说念主物,从孙九皋、陈云九两东说念主年届九十乐龄可推断《荆钗记·开赴》首剧的献艺离《审音鉴古录》1834年的发行至少也有四十年的时辰了。不错确定白丝 跳蛋,《审音鉴古录》的创作年代比1834年要早得多,作者看过首剧的献艺,不然写不出如斯繁复的舞台身体;而若是首剧献艺四十年之后还有他东说念主在舞台上演的话,就不存在“恐失传”的担忧了。一般来说,跟着献艺训戒的积存,演员其后演的频频要比第一场演得好。从书中只提“首剧”,咱们不错觉得《审音鉴古录》的创作年代与孙九皋演《荆钗记·开赴》首剧时辰相仿。那么,咱们不错判断《审音鉴古录》的创作年代早于《扬州画舫录》的发行年代1795年。从汤贻汾的设置年代1778年来看,其时汤尚属年青,《审音鉴古录》不大可能是其所写。策划琴隐翁小引,此书在购回之前,在京城已有发行,看来此言信得过度颇高。但具体何时成书,作者何东说念主,仍是一个谜。
查孙九皋、陈云九都是清代高宗扬州老徐班的成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纪录,两淮盐务在高慢宗弘历南巡时,“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昆腔之胜,始于商东说念主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12](P107)。这些班被称为“内班”,老徐班是扬州昆腔“七大内班”之首起者,扬州完善的昆班也从此时起。据书中纪录,演员陈云九在老徐班是小生变装,孙九皋是外脚副席(后入洪班),而其名见于《审音鉴古录》,看来作者对扬州的戏曲献艺和梨园相当熟悉。不外陈云九是教习的身份,《扬州画舫录》未见说起,只说“程班……正生石涌塘,学陈云九风月一片,后入江班,与朱治东演《狮吼记》梳妆跪池,风致绝世”。教习一般由历年的老艺东说念主担任,可见作者不雅剧时,二东说念主的年岁如故不年青了。
高慢宗第一次南巡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老徐班约在第一次南巡前后启动组建,其后落幕,演员一说念复返苏州,被强令入织造府班。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由商东说念主洪充实创办的洪班,约半数的艺东说念主是由苏州织造府班逃走出来的老徐班旧东说念主[12](P125)。由此咱们不错推断,《审音鉴古录》的成书年代轻便应当在1751年至1795年之间,属于乾隆时刻的剧学文章,而非说念光年间的作品。
三
该书的作者是谁呢?他对扬州的戏曲献艺和梨园如斯熟悉,会不会是梨园中东说念主呢?查阅《扬州画舫录》,卷五提到的有文化的艺东说念主有三位:一位是余维琛,“徐班副末余维琛,本苏州石塔头串客。侘傺入班中。面黑多须,善饮,能读经史,解九宫谱。脾气慷慨,任侠自喜”[12](P122);一位是朱野东,“小旦朱野东,乳名麒麟不雅,善诗,气息出诸东说念主右。”[12](P127);还有一位是董抡标,“抡标,好意思臣子,能言史事,知己律”[12](P127)。余维琛是那时著明昆曲艺东说念主,说起来,与《梨园原》有一定的关联。艺东说念主黄幡绰是余的老诚,弃儒习乐,著成《明心鉴》,文东说念主庄肇奎助其验证补充,更名为《梨园原》;他的弟子余维琛、龚瑞丰又托文东说念主叶元清,加进了他们我方的演艺心得,遂成今天的《梨园原》[13](P7-8)。据此看来,艺东说念主参与《审音鉴古录》编订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不外从书中大量的评点批录来看,作者应当不是梨园中东说念主。《审音鉴古录》的五类评点批录府上波及的内容好多,有科介、穿关、场上位置、说念具、读音、叶韵、板拍、工尺等,讲明作者对戏曲舞台献艺相当了了。在这些评点中,有畸形一部分是特意匡正时弊的,常用的法子是“俗……”、“俗……非”、“莫……”,如《琵琶记·规奴》眉批“俗对正场独唱,不与侍女言非”[8](P30)、“悠闲窈窱,丰韵自生,依此而演,戴鬏古扮,莫换时妆”[8](P29),《西厢记·惠明》尾批“俗云跳惠明,此剧最忌混跳,……莫犯绿林身体,是剧皆宜别之”[9](P653),《永生殿·闻铃》东说念主物上场按语“杂扮一小阉东说念主执曲柄伞随小生上。俗扮马夫拉马,陈元礼随小生上非”[9](P897),《琵琶记·噎糠》旁批“俗作细米非”[8](P70)等等。这些批录一方面讲明那时舞台献艺还有许多不标准的所在;另一方面也讲明不雅众对戏曲舞台献艺作念出的评价。大要进行评价并匡正时弊的东说念主,恐怕不应是台上献艺的艺东说念主,而更有可能是台下不雅剧月旦的文东说念主。
评点批录中,有不少富于文体性的语句,尤其是眉批和尾批。如《永生殿·疑谶》眉批“北曲从硬中英俊,南词在软地风生”[9](P489),对仗十分奥密;又如《鸣凤记·河套》眉批“第一笑如海底雷鸣,第二笑巨风击浪,第三笑鱼跃浪花,此一笑非半载奇功再不行也”[9](P722-723),使用了夸张譬如的修辞手法,来描写演员的“笑”功;《续选永生殿·弹词》以致还用诗歌的体式来注眉批,“制谱至舞盘,锦章片片攒;龟年窈窱曲,师旷料应叹”[9](P911)。而《琵琶记·镜叹》尾批“剧之千百出,曲有万千种,莫难于《镜叹》、《挂家》,最艰于排练,如寻梦玩真,内含情境,外露春生,可增浓淡,点染惟此,二出全在白描,愁苦上作念出个实质东说念主来,当知妻贤子孝可化愚妇愚夫,使不雅者有所感动也”[8](P185),竟似一篇韵味皆备的好意思文,朗朗上口。此外,还有其他许多排比、对比一类的句子。从上所述不雅之,该书的批录者当属文东说念主无疑。而从书中提到的扬州老徐班艺东说念主和剧中大量的“苏白”(时风以此油嘴滑舌)来看,作者很有可能是居住在扬州或者江南一带的文东说念主。
其实,在那时江南一带文东说念主熟悉、爱好戏曲的好多。清乾嘉年间恰是昆曲达到顶峰的时刻,岂论是管事梨园的献艺如故剧学文章的出书,都达到了空前的更生。徐大椿著的《乐府传声》,黄幡绰、庄肇奎著的《梨园原》,玩花主东说念主初选、钱德苍增辑的《缀白裘》、冯起凤编的《吟香堂乐谱》、叶堂校订的《纳书楹乐谱》,铁桥山东说念主等著的《消寒新咏》,焦循的《剧说》、《花部农谭》等都是那一时刻的文章。文东说念主创作的有影响力的作品不是好多,然而也有像江西籍作者蒋士铨在扬州著的《香祖楼》、《临川梦》神话,无锡杨潮不雅的《吟风阁杂剧》,泰州仲振奎的《红楼梦神话》、《怜春阁》等作品。
这一时刻,还有许多文东说念主喜爱昆曲、热衷于过问戏曲活动的纪录。据《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大事年表”[5](P44、46):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南通县石港镇陈邦栋、文正书院院长吴退庵、不雅音阁主抓一懒等三十余东说念主在听渔馆构成樵珊(昆)曲社。”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安徽歙县方成培作念客扬州,不雅看老徐班演《雷峰塔》神话,颇觉辞鄙调讹,遂据艺东说念主献艺本给予改编,十月脱稿。由吴凤山点校行之。”
“嘉庆四年(1799年):仪征李斗在扬州邀友东说念主不雅剧,我方过问献艺。黄承吉作诗记此事(见《梦陔堂诗集》)。”
“嘉庆五年(1800年):武进汤贻汾任京口(今镇江)守备,在丹徒王文治家不雅剧,作长诗记叙所见(《琴隐园诗集》卷二)。”
这些材料讲明那时文东说念主与戏曲的关系口角常密切的,不单是是在戏曲创作方面,在舞台究诘方面同样未作壁上不雅。出于对戏曲的爱好,许多文东说念主不仅喜爱不雅看戏曲,况且从事戏曲创作、改编脚本、组织献艺不雅剧、进行场上疏通,以致兴之所至,还会登场串演,上述东说念主物都属此类。
清中世昆曲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基础,如《扬州画舫录》卷十一纪录的昆曲串客(业余演员),“串客本于苏州海府串班,如费坤元、陈应如出其中。次之石塔头串班,余蔚村出其中。扬州清唱既盛,串客乃兴。王山霭、江鹤亭二家最胜。次之府串班、司串班、引串班、邵伯串班,各占一时之胜”[12](P255);还有《扬州画舫录》卷五所载的颇有神话颜色的东说念主物——“录工尺乐谱十数橱”的程志辂、能指出艺东说念主《琵琶记》工尺不实的胡公、精于调子的“山中隐正人”詹政[12](P136),以及《审音鉴古录》前言提到的王继善和他的父亲琼圃翁等东说念主,他们一般文化头绪较高,对戏曲舞台艺术有着比拟深通的究诘,《审音鉴古录》未尝莫得可能是这一类东说念主中的文东说念主所写。即以《扬州画舫录》而论,作者李斗本一介布衣寒士,若非以《扬州画舫录》传世,其名恐怕不传。而一部《扬州画舫录》,给咱们留住了何等丰富的戏曲史料。
恰是由于艺东说念主、作者、民间的集体参与,才使得昆曲在这一时刻达到顶峰,变成昆曲扮演艺术的“乾嘉传统”,从这个角度注视《审音鉴古录》一书,对咱们今天究诘及保护发展戏曲艺术,不无启发敬爱敬爱。
《审音鉴古录》的作者具体是谁,今天已不可考。不错确定的是,该书的创作年代应在1751年至1795年前后,作者是生涯在扬州一带喜爱昆曲的文东说念主。至于作者为什么不签字,恐怕与那时社会重诗文、轻戏曲的概念不无关联。值得侥幸的是,《审音鉴古录》得以流传下来,为咱们留住了珍稀的戏曲献艺和戏曲审好意思的究诘府上,使咱们今天得以一窥昆曲巅峰时刻的历史真貌;同期,较准确地界定《审音鉴古录》的创作年代、地域和作者,也故意于咱们横向比拟同期期的剧学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那时戏曲舞台和戏曲表面发展作念进一步的潜入究诘。(胡亚娟)
参考文件:
[1]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书社,1986.
[2]廖奔.中国戏曲史[M].上海: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04.
[3]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书社,1981.
[4]郭亮.昆曲扮演艺术的一代范本——审音鉴古录[J].中国戏剧,1961,(Z7):54-59.
[5]《中国戏曲志》裁剪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苏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书,1992.
[6]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书社,2002.
[7]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究诘[M].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4.
[8]审音鉴古录[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第五辑第73册,1987.
[9]审音鉴古录[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善本戏曲丛刊》第五辑第74册,1987.
[10]杨廷福,杨同甫.清东说念主室名又名字号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1.
[11]谭正璧.中国文体家大辞典[M].上海:光明书局,1934.
[12]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M].北京:中国戏剧出书社白丝 跳蛋,1959.
发布于:广东省